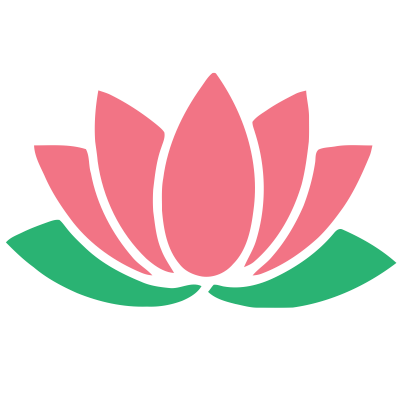猫
郑振铎
我家养了好几次的猫,却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来。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回的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后来这只猫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东西,光泽的毛也污涩了,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想着种种方法去逗它,它都不理会。我们都很替它忧郁。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绫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观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的,懒惰的,郁闷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来,三妹很难过的说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个来相伴的小侣!当时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
隔了几天,二妹从虹口舅舅家里回来,她道,舅舅那里有三四只小猫,很有趣,正要送给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只来。礼拜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同来。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时,它也会扑过去捉。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都很为他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的查问得好几次。每次总要寻找了一回,方才寻到。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我回家吃午饭,总看见它坐在铁门外边,一见我进门,便飞也似的跑进去了。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隐身在阳光隐约里的绿叶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把它捉了下来,又极快的爬上去了。过了二三个月,它会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衣下楼,没有看见小猫,在小园里找了一遍,也不见。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
“三妹,小猫呢?”
她慌忙的跑下楼来,答道:”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
家里的人都忙乱的在寻找,但终于不见。
李妈道:”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它在厅上。烧饭时,才不见了它。”
大家都不高兴,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连向来不大喜欢它的张妈也说,”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以为它偶然跑到远处去,也许会认得归途的。
午饭时,张妈诉说道:”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她说,早上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被一个过路的人捉去了。”
于是这个亡失证实了。三妹很不高兴的,咕噜着道:”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
我也怅然的,愤然的,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取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
冬天的早晨,门口蜷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的,但并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饥饿所杀。张妈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它,它不活泼,也不象别的小猫之喜欢顽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如此的,过了几个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它渐渐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泼。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闲谈着时它也常来蜷伏在母亲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时也逗着它顽,但并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有一天,它因夜里冷,钻到火炉地下去,毛被烧脱好几块,更觉得难看了。
春天来了,它成了一只壮猫了,却仍不改它的忧郁性,也不去捉鼠,终日懒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这是,妻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妻常常叮嘱着张妈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
妻道:”张妈,留心猫,它会吃鸟呢。”
张猫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楼时,听见张妈在叫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没有了,笼板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羽毛松散着,好像它曾与它的敌人挣扎了许久。
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于是立刻便去找它。
妻听见了,也匆匆的跑下来,看了死鸟,很难过,便道:”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它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妈要小心了。张妈!你为什么不小心?!”
张妈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
于是猫的罪状证实了。大家都去找着可厌的猫,想给她以一顿惩戒。找了半天,却没找到。真是”畏罪潜逃”了,我以为。
三妹在楼上叫道:”猫在这里了。”
它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阳,态度很安详,嘴里好像还在吃着什么。我想,它一定是在吃着这可怜的鸟的腿了,一时怒气冲天,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它很悲楚的叫了一声”咪呜”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里还愤的,以为惩戒得还没有快意。
隔了几天,李妈在楼下叫道:”猫,猫!又来吃鸟了。”同时我看见一只黑猫飞快的逃过露台,嘴里衔着一只黄鸟。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
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辨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
我很象补救我的过时,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我将怎样的对它表白我的误解呢?
两个月后,我们的猫忽然死在邻家的屋脊上。我对于它的亡失,比以前的两只猫的亡失,更难过得多。
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
自此,我家永不养猫。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于上海
曾收录老中学课本
小麻雀
老舍
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 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 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熟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 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 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它的翎羽。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它的举动与表情 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它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它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倚靠。它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 我想拿几个饭粒诱它前来,又不敢离开,我怕小猫来扑它。可是小猫并没在院里,我很快的跑进厨房,抓来了几个饭粒。及至我回来,小鸟已不见了。我向外院跑 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蹲着呢。我忙去驱逐它,它只一扑,把小鸟擒住!被人养惯的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与爪在猫嘴旁搭拉着,和死去差不多。
瞧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到西屋。我不敢紧迫,怕它更咬紧了可又不能不追。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我还没忘了那个眼神。那个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神。那个眼神与我的好心中间隔着一只小白猫。来回跑了几次,我不追了。追上也没用了,我想,小鸟至少已半死了。猫 又进了厨房,我楞了一会儿,赶紧的又追了去;那两个黑豆眼仿佛在我心内睁着呢。
进了厨房,猫在一条铁筒–冬天升火通烟用的,春天拆下来便放在厨房的墙角–旁蹲着呢。小鸟已不见了。铁筒的下端未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儿小猫用脚往里探。我的希望回来了,小鸟没死。小猫本来才四个来月大,还没捉住过老鼠,或者还不会杀生,只是叼着小 鸟玩一玩。正在这么想,小鸟,忽然出来了,猫倒象吓了一跳,往后躲了躲。小鸟的样子,我一眼便看清了,登时使我要闭上了眼。小鸟几乎是蹲着,胸离地很近,象人害肚痛蹲在地上那样。它身上并没血。身子可似乎是蜷在一块,非常的短。头低着,小嘴指着地。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 顶大的楞着。它只有那么一点活气,都在眼里,象是等着猫再扑它,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又象是等着猫赦免了它,或是来个救星。生与死都在这俩眼里,而并不是清醒的。它是胡涂了,昏迷了;不然为什么由铁筒中出来呢?可是,虽然昏迷,到底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生命根源的,希望。这个希望使它注视着地上,等着,等 着生或死。它怕得非常的忠诚,完全把自己交给了一线的希望,一点也不动。象把生命要从两眼中流出,它不叫也不动。
小猫没再扑它,只试着用小脚碰它。它随着击碰倾侧,头不动,眼不动,还呆呆的注视着地上。但求它能活着,它就决不反抗。可是并非全无勇气,它是在猫的面前不动!我轻轻的过去,把猫抓住。将猫放在门外,小鸟还没动。我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是没受了多大的伤,虽然胸上 落了点毛。它看了我一眼!
我没主意:把它放了吧,它准是死?养着它吧,家中没有笼子。我捧着它好象世上一切生命都在我的掌中似的,我不知怎样好。小鸟不动,蜷着身,两眼还那么黑,等着!楞了好久,我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 上,看着它,它又楞了半天,忽然头向左右歪了歪用它的黑眼睁了一下;又不动了,可是身子长出来一些,还低头看着,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曾收录老中学课本
a pair o shoes
Last week I was invited to a doctor’s meeting at the Ruth hospital for incurables.In one of the wards a patient,
and old man,got up shakily from his bed and moved towards me.I could see that he hadn’t long to live,but he came up
to me and placed his right foot close to mine on the floor.
“Frank!”I cried in astonishment.He couldn’t answer as I knew,but all the time pressed his foot against mine.
My memories raced back more than thirty years – to the dark days of 1941,when I was a student in London.The scene was
an air raid shelter,in which I and about a hundred other people slept every night.Two of the regulars were Mrs West and
her son Frank.
Sharing wartime problems,we shelter – dwellers got to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Frank Wwst interested me because he
wasn’t normal,not even at birth.His mother told me e was 37 then,but he had less of a mind than a baby has.His speech
consisted of rough sounds – sounds of pleasure or anger – and no more.Mrs West,then about 75,was a strong,capable woman,
yet she had to be of course,because Frank depended on he entirely.He needed all the attention of a baby.
One night a policeman came and told Mrs West that her house had been flattened by a 500 -pounder.She lost neerly everything she owned.
When that sort of thing happened,the rest of us helped the unlucky ones.So before we separated that orning,I stood beside Frank
and mesured my right foot against his,They were about the same size.That night,then,I took a pair of shoes to the shelter for
Frank.BUT AS SOON AS HE saw me he came running and placed his right foot against mine.After that,his greeting to me
was always the same.
雨中的命和命中的雨
我和你们一样,对于常耕地这个名字很陌生,如同在乡下野坟地的一块粗糙墓碑上看到的一个名字。
我是听一个朋友讲的,我的朋友是听他的一个朋友讲的,他的朋友是听他朋友的朋友讲的……
追查下去,这个故事出自一个女法医之口。
于是,一切到了我这里,都变得十分遥远了。
我想,你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每逢下雨的日子,你都会打个冷战,蓦地想起常耕地这个名字。
几年前,常耕地这个名字在这个古城可谓无人不晓,这也许是他普普通通的人生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了。
不过,很快的,一切都像他那条简单的生命一样,随风而去,不留一丝痕迹。
我们还活着,而且据说未来还很漫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慢慢回放常耕地的一些经历,现在让我们回到他的童年时代。
常耕地出生在一个小村子,他爹给他取了这么个动词名字,也许是因为他爹除了耕地再不会干别的了。
也许是老天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这名字控制了他的一生。
他挣扎过,奋斗过,但结局是换来了政府的一粒枪子。
常耕地出生的那天,下雨。他的第一声并不嘹亮的哭声被淹没在哗哗的雨声中,没有引起除了他爹娘以外的任何人注意。
就这样,常耕地默默无闻地来到了这个人世间。
大约在他六岁那年,他娘死了,那天也下雨,常耕地看着一群人把娘抬走了,却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凄冷的雨中,白色的灵幡和猩红的棺材格外醒目。
那送葬的队伍越来越远,而常耕地则麻木地坐在门槛上,只是呆呆地望。
不久,爹领着他,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来到了另一个村子。
爹把他交给了一对没儿没女的老夫妻,转身就走了。
天又下起雨来。
透过雨帘,常耕地紧紧盯着爹越来越小的背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一次头看看自己。
他不知道爹把他抛弃了,他不知道他从这个雨天起直到二十年后被枪决再没见到爹一面。
他什么都不知道,正像此时观看他一举一动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一样。
常耕地转眼长大了。
而这个时候,他的养父早已经死去,只有他和养母相依为命。
一年, 武装部到村里征兵,常耕地报了名。
他的身体像牛一样健壮,顺利地通过体检,得到了一纸通知书。
离开村子那天,老娘送他。
天阴了,冷雨冷雪漫天飘落。常耕地回过头,看见老娘孤零零立在雨雪中,花白的头发不停地抖动,眼睛就湿了,他一步一回头地上了路。
三年军旅生涯,没能改变常耕地的命运。
退伍后,他又回到了那个村子。
后娘已经死了,他成了一个孤哀子。
生活一如从前,还是常耕地种地,吃了睡睡了吃。
因为穷,村里没有女人嫁他。
有一天他没事,到村子外闲转,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一个错误的时间遇到了一个错误的人。
错误的人真挚地对他说:“常耕地,你去抱几个俑头吧,我给你钱,你就不用种地了。”
那个村子离一个举世闻名的古墓很近,当时那里的文物刚刚发掘和修复,管理体系还不完善。
于是,常耕地就乖乖地去抱俑头了。那夜月黑风高。
当他第三趟抱着俑头返回村子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他暗暗高兴,因为大雨一冲,脚印就没了。
那两个人只给了常耕地很少一点钱,靠这点钱是不可能让他彻底摆脱黄土地的。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不久,常耕地在县城火车站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戴着红袖标,维持秩序。
一天, 他正在站台上工作,天又下起雨来。
这时候,他已经能够预感到什么了,抬头看看天,抖了一下,自言自语道:“难道又要出什么事吗?”
刚说完,一副冰凉的手铐就铐在了他的手腕上。
本来,常耕地被判了有期徒刑,不幸的是,后来又改了,死刑。
枪决常耕地的前几天,一个女法医去了他的大牢。
脸色苍白的常耕地羞赧地说:“我是活不了几天的人了……想跟你说一会儿话,能行吗?”
女法医有点犹豫。
常耕地叹口气,说:“如果你不听,那我这些话就再不会有人听了……”
女法医的心有点酸,点点头:“你说吧。”
常耕地抬头望着屋顶,慢慢讲起了他从小到大的经历以及那时不时就出现的雨。
终于讲完了,他乞求地看着女法医,说:“我没有一个亲人,死后尸体都没人收。你是我最后见到的一个人,我只求你,在我死后,你走到我身边看我一眼,看我一眼就行了……能行吗?”
女法医低下头去,挤出两个字:“能行。”
常耕地凄楚地笑了笑。
有一天,女法医从市场买菜回来,骑单车走在街上,突然天空一声霹雳,大雨就泼下来,她陡然想起–今天枪毙常耕地!她顿时目瞪口呆。
一切都晚了……
常耕地死了,像他的出生一样无声无息。他最后的一点要求没能实现。
我的朋友向我讲起常耕地的时候,也是下着雨。
我觉得这个雨天和常耕地悲剧的一生不断出现的奇怪的雨天已经毫无关联,只不过是淅淅沥沥的冷雨让我的朋友想起了他罢了。
很快,人们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活着的人还活着,这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他们–或者说我们–依旧挤公共车、和情人约会、和商贩讨价还价、携妻带子到野外度周末……
只是,雨还会落下来,飘飞在每个人的头顶。
曾青年文摘 2005年6 彩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