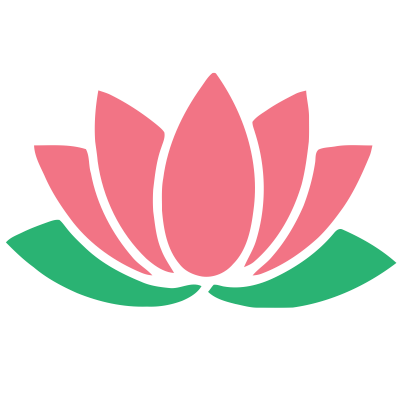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新版《红楼梦》的失败,连上帝也看见了。
快进,画外音旁白,鬼魅般吓人的音乐。
演员有形无神,有的连形也不具备,不在现场的表演,仿佛是一场例行走秀,华丽的道具,唯美的服饰,一场煞有介事的重拍。
《红楼梦》就这样被重拍了一回。神韵皆失,徒留一场喧闹。
他们就这样动了名著。这样一部千疮百孔,用李少红的话“哪里都有不足,所有的都是遗憾”(见新京报9月16日报道)的电视剧,竟被红学家冯其庸嘉许为“又一次涌现了高峰,可以跟原先的87版的《红楼梦》并称。”
这是买通《红楼梦》拍摄权的利益集团的大胜利。御用“红学家”是其中最大的精神赢家:他们显示了自己的权力,过足了文化顾问的瘾。
胜利者在暗自窃笑。几乎一致的“恶评”,却不意做成了营销,投资人赚得钵满盆满,演员们一夜走红。
失败者好像只有委屈不已的女导演李少红。
由商人罗立平发起的重拍,在官办协会的帮助下,靠看不见的手的协助——在广电总局的保驾护航下,六七年不拍而能保住“题材”,阻止了觊觎者和竞争者。然后与北京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做成一个局,再加上垄断影商韩三平的加盟,最终以垄断的方式获得了利益最大化——超级垄断利润。
隆重的集体创作方式,是该类作品官方属性的最好表征。
多达二十人的顾问名单,凸显着操盘手运用意识形态把门人的超强能量。这些颇有来头的顾问们,平日里经常出现在请示报告、观片会、评奖会、以及稠密的调研活动上,一颦一笑都将决定一部作品的生死。他们不是专业的鉴赏家,而是专门的审判者。看是为了定性,他们能从一个微不足道的镜头里窥见沉船般的政治风险,也能从平淡无奇的作品里发现巨大的精神力量。那是些让导演、制片和投资人心惊肉跳的名字,不,几乎就是上帝。
在总导演总策划下面,是做顾问的“红学会”。
该会公布的宗旨是,“鼓励会员努力学习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从事《红楼梦》学术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工作。”名义上,“红学会”是靠挂在官方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下面的民间学术团体,但它跟各类“民间学术团体”一样,从来都不会是民间机构,而是准官方性质的审查机构——他们协助负责文化作品的政治把关,力图将对某一作品阅读研究的阐释权控制在手里。那些不宜以指令方式下达的命令,通过这些门类齐全的各色协会学会,笼罩了民间的研讨空间。自发性的研究,在这样的准衙门面前,要么归顺,要么自取灭亡。
看看“红学会”对新版《红楼梦》的操控就明白了,红学家们似乎掌控了生产过程。
首先是阐释权的把持。据李少红说,之前有一个剧本被红学家否决了,理由是不忠实于原著。120回还是80回,事关对原著的理解。给《红楼梦》定调,貌似学术问题,实则牵涉文化利益。用崔文华先生的话说,就是阐释权的“变现”。李少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说法足以证明这一点,出品方请的三位红学家“给我上的就是120回的课,我们实际上谈不上编剧,也谈不上改编,就是把120回的小说编成50集的剧本,所有的取舍都是在红学家的意见下进行的。”
拍87版《红楼梦》的时候,是力主80回的周汝昌一派占了上风。现在则翻了个个,120回派胜利了。
“红学会“的“红学家”,他们一定会贯彻自己的意志,绞杀一切不符合集体意志的东西。
具体改编完全按照红学家的意见办事:“120回的原著根据红学家的意见完成删减归纳分集,”在这样的统制下,最需要想象力和个性的创作,沦落为繁重的“体力活”。《南方周末》的报道称,在某“文学顾问”的统领下,九个不到三十岁的80后,像农民工一样编写剧本。他们在规定框架内戴着镣铐跳舞,完全变成了工匠。这些人或可称之为“文化奴隶”,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任务。文学统筹“负责润色统一风格后,最后红学家审阅”。
对演员的要求,红学家也不肯通融。“红学家非常坚持演员要靠近书中的年龄。”李少红说,“书中贾宝玉出场时只有九岁”,她设想起码得在十五六岁,这样恋爱起来才合适,最后与出品方和红学家达成的共识是“十四岁”。甚至连演员的选用也得得到红学家的首肯。
于制片方和出品方与红学家达成一致,在50集的长度里拍120回,既保证了红学家的阐释权,又满足了投机资本对产出利润最大化的要求。
如此一来,在号称以“亿”为投资基数的活动里,除了一千多万演员片酬外,主要花在道具和布景上,“因为全剧使用全套电影摄影机镜头拍摄,所以对书中所描写的贵族家庭奢华的生活,细致入微的吃、穿、用等东西在拍摄时都是尽可能的还原真实,因此造价也极高。”制片人李小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光摄影棚就有12个,其中最大的是5000平方米的贾母前院……剧组还参照原著搭了90多堂场景。”这就意味着,花在电视剧一剧之本上的精力和金钱少之又少。
在资本和红学家的双重掣肘下,导演李少红不过是个领工者罢了。留给她的只有雕虫小技的发挥空间了。而且,投机资本要求她以急行军的速度完成生产。87版《红楼梦》用了近两年时间,筛选演员,并先后举办了两期红剧演员学习班,“让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自己的情趣,最后确定角色。”新版《红楼梦》筹备期长达近六年,但选秀活动实际只用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演员培训的期限仅有区区三个月而已。培养演员们贵族气质的途径,是让他们住进豪华宾馆。
投资人规定50集解决问题,红学家要求在50集里交代全部的内容,李少红只有快进和画外音。麻烦的还有,李少红还得接收来历暧昧的指令性演员及投资人通过“海选”扶植起来的一系列演员,李少红于是又只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换掉一拨刚刚为观众熟悉的面孔——代价是造成观众认知的断裂。
资本和文化霸权控制下的创作如此残酷,是李少红没料到的,也是观众想象不到的。其实,这种文化生产方式一直就未改变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诗歌大跃进到如今的文化创意大跃进,一直就只是领导意志的喧嚣。他们通过这种运动组织方式,目的就要把“我”变成“我们”,制造一个个气势宏大、色彩艳丽、动作划一的文化产品,填充被需要制造出来的“胃口”。权力永远有能力支配一切。那些平庸、丧失了生命力的仿真品,仅有一个功效——显示政府的动员能力、威权效率和再造“和谐”社会文化氛围的意志。
资本与权势的联手,使得名著成为赚钱的工具,没有世界观、文学观、价值观,一切都是赚钱的筹码。
但他们还要哭穷,声称自己是花钱推广古典名著。针对他们含含糊糊虚虚实实的“账本”,资深网友“规划员K”在天涯论坛发帖,进行了一系列精确分析,给出了一张收益结算:投资额由“5000万”变作“1.18亿”,某段时间又号称高达“2亿”的大项目,为垄断利益集团吸金无数。他们实际投资只有5800万,收益可达1亿到1.5亿(目前已经收到8500万)。“就好比投资100块钱,已经收到146块,未来最多可能受到258块。”
他还戳穿了该利益集团撒谎的“真相”:按照出品方的说法,每集拍摄成本在236万至260万之间,260万/集乘以50集,就是1.3亿;1.18亿除以50集,就是236万/集。即使按照他们的说法,每集可支配的资金也只有236万,如果按上限260万计,那多余的1200万从何而来?他认为,利益集团把“成本”等同于“投资”——把“借方”和“贷方”的某个项目调了个方向,“大赚特赚”的事实就变成了“赔本”和“入不敷出”了。号称每集成本花了236万至260万,而业内人士认为100万已是极限。
而利益方的收益相当可观:当初北京电视台以30万/集、共计1500万获得的新版《红楼梦》首播权,仅广告费一项就相当可观,还不算当年那场“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带来的超过千万的广告收益,该台公布的《新版〈红楼梦〉营销侧记》显示,带来新增广告创收近2000万元,北京电视台可谓名利双收。拥有发行权的华录百纳收益已经达到了6500万元人民币。至于中影集团,也一定会赚得钵满盆满。
重温两位操盘手的豪言壮语,或许能找到该片失败的某些根由。执行制片人、华录百纳副总罗立平,为新版红楼梦的定位是“贵气、养眼;在绚丽、唯美的背景下,贵族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混世魔王贾宝玉从泛爱到专一。”如此这般对《红楼梦》主题的界定,已经将一部丰富多样的名著拧成了干巴巴的教条。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为了避免拍成“暴发户”而找到了“艺术家”韩三平。以运作主旋律影视著称的韩更是豪气万千:“要通过重拍红楼梦,终结韩剧在亚洲的垄断地位,《红楼梦》要‘一鱼两吃’”。这般自负、决绝的架势,足以令“奇迹”涌现。
“华丽”或许是,但那是空洞的华丽,或许称奢靡更合适些。他们不明白,仅仅用钱和决心是无法堆出艺术的,场面似乎都有了,该拍的一场都未落下,但就是不能感动人,不能让观众从中获得那种震颤的美的体验。不拍人的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红楼梦就变成了场面戏,形似神亡。
“《红楼梦》这三个字就是钱。”罗立平这句话道出了执意拍新版《红楼梦》的“秘密”。
《红楼梦》这个影视题材的运作过程,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其实就是私人利益集团对国民财富的强势瓜分。真正的创意、灵感和能力,在此新型托拉斯面前不堪一击。“题材”本身和书号台标一样,是可以交易流通的硬通货,文化管制制度衍生的寄生虫们,谈笑间身家翻飞。
从《建国大业》开始,某些“艺术家”豁然开窍,发现了名利双收的新路径:那就是与政府携手,与国有垄断企业联手,一起进行主旋律产品的大规模制造。明星云集,舆论开道,行政清场,公款托底,轻松赚银子,参与者利益均沾。这个游戏的核心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们齐心协力把文化创意产业做成了文化垄断。这种资本盈利新模式,养肥了一批文化投机客,苦了无辜的观众——在这些伪劣产品的狂轰滥炸下,历史被扭曲,审美神经萎缩,人们变得只能接受或欣赏那种被制造出来的“红色需求”,被绑架的永远是善良的人民,他们的每一次收视成就了资本家和文化商人的敛财梦。真与艺术渐行渐远,民众最终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买单者和受害者。一个粗鄙的心,难以分辨美丑、真假,看的只是热闹。在热闹复热闹的文化游戏的包裹下,但愿他们感觉到了盛世的幸福。
此时,台湾学者蒋勋不合时宜地来了。他的旨在教人回到文本,从而发现文学魅力所在《红楼梦》解读适时地出版了。不愿被意识形态格式化的心灵,或许可以借助他细腻的点拨,最终穿破“红学家”设置的藩篱,走向让人性获得滋润的文学深处。
集体下的蛋,与蒋勋先生一个人悉心孵化的蛋,都摆在大陆民众面前,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