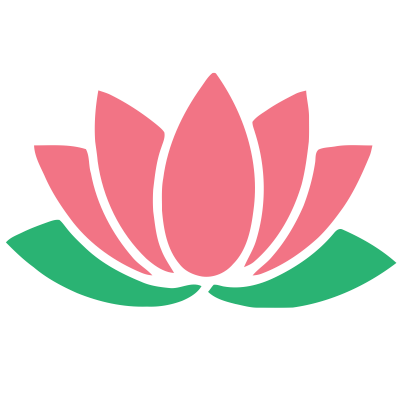想父亲
阎连科
想父亲,摘自《河南日报》阎连科
我的父亲有15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了。不知道他这15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 啥。可是我,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我每每想起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到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读小学。学校在镇上,在镇上的一座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前,父亲都千方百计存下 几块钱,把这几块钱全都换成一沓儿簇新的一毛的角票儿,放在他睡的枕头的苇席下,待大年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 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角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 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一张,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胆大,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 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打我,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我说没有,父亲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设有,我说没有,父亲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 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父亲又朝我脸上打了一耳光。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了,只记得父亲在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手的。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实在 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的。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去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了,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了哩。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不看我,也不 看我哥和姐姐们。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 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父亲也 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哩,待人家走了后,父亲把大门闩上,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地上,先劈里啪啦把我打一顿,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 为我真的没有份,我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劈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 虚的土地一个模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有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上床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去把我摇醒来,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 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父亲就拿手在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子外。看一会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 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坐着。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想了啥,30年过去了,我 还是不知道父亲到底想了啥呢。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岁了,到公社大院里去玩耍,看 见一个公社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连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父亲问: “在哪儿?’”我说:“就在公社大院的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高尚纯洁的人,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口,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 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我不知道为啥,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什么模样 儿。直到十余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 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哩,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我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我把脸扭到一边去,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 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还是头题呢,家里墙上糊的报纸上,正有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 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铝盒在银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 的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和我的名字上,却被许多的手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15年了。在这15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的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 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至今我没有为那次偷盗懊悔过,只是觉得,父亲 要能对我痛打上三次、四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骂我就好了。当一个作家有什么意义呢?能让父亲如往日一样打我吗?不能哩,不能当作 家有什么意义呢?
5年前,我的孩子九岁半,不停地从家里偷钱去买羊肉串,吃得他满嘴起燎泡,发现后我让孩子跪在水泥地板上,一个耳光一个耳光往他的脸上掴,从此后,我就再 也没有打过我的孩子了。今年他上初三,有次考试本应考好的,可是没考好。没考好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爸爸,你打我吧,你为啥不打呢?你为啥不打我 呢?你应该打的呀!”今年我出差回家,正赶上给父亲上坟,站在父亲的坟前,拉着坟前泛青的柳枝,想父亲如果能手持柳枝从坟里出来打我该有多好哟,那是多么 慰心的生活哟。
初载于《河南日报》
后载于《读者》2001.20
背影
作者: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澹,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棚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选自《背影》,1928年10月,亚东图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