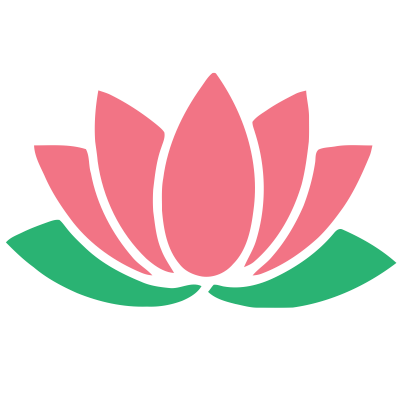作者:思凝 来源:人之初
冥冥宇宙,渺渺茫茫,仿佛有一种既无形又无名的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使我的情爱具有悲剧的色彩。
我是一个学过采矿专业的中学教师,今年60岁了。作为一个从教37年、即将退休的山村穷教书匠来说,能说服自己参加“有情人难成眷属”征文活动,确实需要勇气。这就算是对人生的一次小结吧。
1960年,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其时,我是一个来自湖南的出身不好、家境极差的农村学生,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时已饿得全身浮肿了。我主动要求到祖国的边疆内蒙古锻炼改造自己。
我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煤管局属下的矿业学院筹建处工作,不久就参加了煤炭部组织的黄羊捕杀队,以补充人民生活的肉食来源。一年来的草原追猎生活使我粗壮起来,像一个真正的“蒙古猎手”。
由于劳累和水土不服等原因,许多队员都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肠胃病,随队的张医生也病倒了,药品和子弹也用完了。为此,煤炭部专门从北京红十字医院为我们请了一位研究温带草原传染病的苏联博士。由于我精通俄语,队长要我开着吉普车去满洲里车站接人。
等我赶到车站时,火车已开走一个多钟头了,空荡荡的车站只有一个既像蒙古人又似苏联人的高挑女人,她身边放着一大堆行李。在我的想象中,苏联专家应该是一位两鬓夹着银丝的老头儿,所以根本就没理她。等我转了几圈回来,不得不试探着用俄语问她时,天色已近黄昏了。
她大发脾气,骂我是蠢猪,命令我将行李搬上车,而她自己却在一边悠闲地抽着烟。我气不过用中文回敬她一句:“杂种!”
一路上我们谁也不开腔,任凭风儿在耳边呼啸。我赌气将车子开得飞快,渐渐地她的脸上露出笑容,似乎很满意我的疯狂……
天啊!一具横死的骆驼让吉普车真的飞上了天!我慌了,负疚地向她道歉。她突然用比我这个湖南人标准流利得多的普通话说道:“少废话,把我的上衣脱掉,把我脱臼的左臂端好!”“别怕,向上用劲,向上……怎么笨手笨脚的?同志哥,你现在是救人,不是调戏妇女!对,就这样,好了。”
入夜,风从草叶上吹过,发出瑟瑟的响声,从湖的那边飘来了如纱似梦的薄雾。燃着的篝火已灭,狼群就在附近嚎叫。我冻僵了,无奈地走向吉普车。
“快上车!把车灯打开!”她端着冲锋枪,急切地向我喊。一群野狼追赶着千百只黄羊潮水般向我们涌来。我们拼命用冲锋枪狂扫,顿时,黄羊倒下了一大片。狼群在远处停下来,围着被撞坏车灯的车子长啸,不敢靠近。
第二天,我们扔下车子、黄羊和药品,徒步走了一天回到营地搬救兵。队长足足骂了我半个钟头。好在她一再声明是她开的车,并且说我一个人打死了那么多黄羊,可以将功补过,队长这才原谅了我。他把女专家安排在离我的地铺不远的空地上,拉上帘子作为分界,命令我照料好她的生活,当她的勤务兵。
由此,我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她叫斯美塔娜,是苏籍蒙古人,比我大3岁。她父亲是蒙古人,中共地下党员,曾被派到苏联某矿业学院学习,娶了一位俄国贵族出身的空中小姐。解放后,她父亲携俄国妻子和独生女儿回国,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抓工业。斯美塔娜在莫斯科长大,10岁起便在北京求学,是名副其实的“杂种”。她笑说她很自豪,因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杂种是优秀的。
斯美塔娜的美是一种成熟美,而且总带点刺。她为人豪爽,抽烟喝酒,骑马射箭,样样都行。队里的人都很喜欢她,他们都奇怪我这个未婚男人为什么不追求她,他们早看出了,她对我有点意思。
我也总是暗地里骂自己怯懦。
黄羊捕杀队就要撤离,告别晚会上,大家尽情地围着篝火又唱又跳,所有的人都喝足三大碗酒。子夜时分,队长吩咐我和斯美塔娜放哨。我俩都明白,他是让我们有机会单独呆一会儿。
她两眼凝视着远方,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突然若有所思地用俄语问我:“你对我有什么看法?”我马上注意到她用了“你”字。在俄语中,只有对非常亲近的人才用“你”字。
“你是一盆野玫瑰,浑身上下都是刺,但在我心目中,你仍是一朵最美丽鲜艳的花。”我像小学生背书一样说出心里话。
她似乎有意不接我的话茬:“你要回呼和浩特了,我也要去莫斯科办点私事,我会想你的。你会想我吗?”
我很坚定地回答:“会。”
第二天,她大方地和队员们吻别。最后,走到我跟前,用一双大而亮的眼睛盯着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不敢,却只想哭。我狼狈地拨开众人,跨上马向草原奔去。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身后,传来一串笑骂声,斯美塔娜执着马鞭领着队友们追了上来。我拼命向山岗上跑,直到我被她抽打得从马上摔下来。
看热闹的人散去了,她跪下来察看我是否受伤。突然,我有种冲动,把她紧紧拥在怀中……
转眼就到了1962年8月,在内蒙古人民医院的一次联欢晚会上,斯美塔娜身着天鹅绒晚礼服,亭亭玉立地站在了我面前,让我惊喜万分。她兴奋地告诉我:“你绝对想不到吧,我已经借调到这个医院工作了!”那天晚上,我们是舞会的王子和皇后,我们尽情欢乐,庆祝我们的重逢。临别,她深情地吻着我,约我第二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水塔下见面。
翌日,夜幕降临时分,我匆匆赶到水塔下,她正哼着俄罗斯民歌《山楂树》:“啊,茂密的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啊,山楂树,亲爱的山楂树,你为何要忧伤?请你告诉我,勇敢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月光下的斯美塔娜就像歌里唱的一样,那么忧伤,那么美丽。
她很犹豫,眼里透着迷茫:“你喜欢结过婚的女人吗?”“喜欢。你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说过吗,世界上只有寡妇才有资格谈恋爱。我喜欢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谢谢。我就是结过婚的女人,但不是寡妇,你敢娶我吗?”
“敢。”
她把我紧紧抱住,在我怀里哭了起来。
“明天是我的生日,请你到宾馆来,我母亲想见你。”
这是一个星期天,我准时赴约。
斯美塔娜穿着一件领口很低的真丝高档连衣裙,很优雅地坦露着像白玉一样光滑细嫩的脖颈和臂膀,她正在往花瓶里插一束红色的玫瑰花,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异国情调。我们俩相对而坐,静静地听着德沃扎克的《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我们都喜欢德氏的作品,尤其是这第二乐章的慢板。那对祖国故土的深沉思念,那淡淡的忧伤,那宁静而平凡的愁绪,深深震撼着我们的灵魂。现在想来,这是否预示了我和她的这段情从一开始就会倍受磨难?
生日聚会是她母亲张罗的,这个俄罗斯贵妇要亲眼瞧瞧让她女儿鬼迷心窍的乡下人究竟好在哪儿。可是做父亲的一听就极力反对,拒绝与我见面。任性的女儿第一次把父亲撇在一边,另外在宾馆里庆祝生日。
上个月斯美塔娜回了趟莫斯科,与分居多年的丈夫龙浪斯基正式离了婚。他是她父亲初恋情人的儿子,比她大6岁,人很帅气又聪明绝顶。可惜他对什么都无所谓,玩玩而已。迫于家长的压力和青梅竹马的情分,他对她算是爱得比较久,但是,他从没让她有过安全感。
斯美塔娜的母亲坚决支持女儿离婚。她对我第一印象不坏,嫌我是地主出身,不嫌我是个家居农村的普通汉人大学生。
那晚,气氛很好,我们三人都喝了酒。她母亲带着醉意先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
房间里真热,斯美塔娜脱去了连衣裙。啊,我看见了什么?白色尼龙连衣裤里紧裹着的分明是一尊维纳斯雕像!
顿时,我心跳加速,喉咙里像燃着一团火。我们紧紧拥抱。从此,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我对我们的关系很有信心,与她交往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开始考虑婚姻问题。我发现,她与我越亲密,对生活的态度也就越积极,在她父母和我面前就越能表现出自尊与宽容。我们忘情地投入到对方的生活中,充分享受着人间美好的感情。
可是,我们的结婚申请却因为她父亲的干预,迟迟批不下来。
美梦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的日子十分无奈。照我的本意,最好是生米成熟饭,迫使她父亲点头、开绿灯。可是,如果我们太放肆,全然不顾他老人家的意志,那么他肯定饶不了我。他要我们好好考虑,煤管局领导还是他的部下呢!
他父亲的一句话,就像是一块盾牌,无形之中,隔离了我与斯美塔娜的情和爱。我们都感到,得不到结婚证,是生活中最大的阴影。这个阴影总也挥不去,心底的欲望无法排解,我和斯美塔娜都患了精神忧郁症,我们很清楚,长期下去,我们都会毁了。
为了尽快得到那张能释放我们的红色证书,她毅然去了北京苏联大使馆,想通过各种关系,让两个相爱的人能够结合。
但是,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她在北京一个月也没有任何结果。残酷的现实使绝望的斯美塔娜悟出许多道理。她不再忧郁,她告诉我,要自己拯救自己。
从北京回来,她就恢复了以往的自信与开朗。她常鼓励我,要我在心灵上满足她,她会永远做我的好妻子。她说,她爱我,我使她由龙浪斯基的动物变成了一个高尚的女人,我使她感受到了做女人的尊严和幸福,我使她充满自信,使她觉得活在世界上真好!受她的感染,我顿时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起来,似乎所有的障碍都不那么可怕了。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调节自己的情绪。
然而,我们毕竟年轻,还很幼稚。我们这样做,不仅伤害了她父母,其实也伤害了我们自己。
她怀孕了。于是,她正式通知父母,要摆酒结婚,要按东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
她父亲勃然大怒。作为父亲,他心疼女儿;作为领导,他希望我们不要为了私欲毁了自己的前途。他多次暗示我,煤管局领导看在他的面子上,同意对我网开一面,暂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要我好自为之。考虑再三,权衡利弊,我有些害怕,竭力劝她堕胎:“只要我们结婚证能批下来,到时生孩子也不晚。现在不是时候啊!”
斯美塔娜气愤到了极点,她大骂我没骨气,说只有生下孩子,才能软化父亲的硬心肠,才能拿到结婚证。唉,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真不知谁对谁错。
从医院回来后,我们终于闹翻了。她一气之下,回莫斯科去了。
分离,让我们饱尝思念之苦;思念促使我们的心灵更加靠近,我们是完全不能分开的两个人啊!
这就是缘。
于是,一年后,斯美塔娜又辗转回到了呼和浩特。经过了一次变故,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一分一秒。
但是,我却被突然调离呼和浩特,理由是矿业学院缓建,为了不浪费人才,安排我到适合的岗位发光发热。就这样,我来到地处偏僻、条件极差的某煤矿当上了技术员。至今,我一直认为这是她父亲使用权力的结果。
我们的爱恋艰苦而又执著。每个星期六,斯美塔娜都说服母亲派车,跑5个多小时的路,带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到煤矿和我共度周末。
我们小心地品尝着难得的幸福。生活中,我们丧失的太多太多,唯有这爱情维系着我们的生命,拥有它,便拥有了一切。
平平静静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身心充分放松下来。反正我已下放到了基层,前途渺茫。有她的爱情滋润,我已别无所求,我希望就这样生活下去,直到永远。
或许是我太得意了,看不出平静之中的波澜起伏。对我们越来越亲密的交往,她父亲最后还是忍不住拍案而起,要将我绳之以法。在这倒霉的时候,她母亲也突然倒向她父亲一边。老太太说他不能容忍我没出息,让女儿与我保持这种不明不白、不伦不类的关系。我的老天,我真冤枉,难道我愿意这样吗?
斯美塔娜为了保护我,很冷静地主动提出,要和她父亲脱离关系。她身揣苏联护照,如果执意要做什么,父亲还真的管不着。
斯美塔娜怀着一颗受伤的心,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一声不响地直奔煤矿来与我结婚,住在我那间极其简陋的窑洞里。
我们终于在一口锅里煮饭,在同一个口袋里拿钱花,在同一个屋檐下避风躲雨了。日子虽然很清苦,却很快乐。回想起来,这种不顾一切的做法其实并不妥当,然而,当时,我们确也想不出其它的法子。
她的父母不再供给她一分钱、一两油,而我还要省下钱和粮票寄回老家帮补父母和弟妹。我们俩都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为了得到下井补助,我每天都要拖着虚弱的身子下井,好几次都晕倒在井下的巷道里。同事们说,他们经常看到斯美塔娜暗自垂泪。
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味一下梦想中的日子,现实就已经非常无情地做出了决定。
她越来越忧郁。她的护照很快就要到期了,研究工作早已结束,在那种形势下,留下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一切都是那么无助。她对我们的将来失望极了,体质也一天比一天差。
不可回避的日子终于来了。那天,她母亲从呼和浩特赶来接她,一进门,俩人就抱头痛哭。老太太不停地骂我和她自己的丈夫。我只有站在一旁发呆。对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重要的事情,我的个人力量都是不起作用的。
斯美塔娜走了,她带走了我的灵魂,而我似乎只剩下一副躯壳。
我最怕日落,因为黄昏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漫长而漆黑的不眠之夜在等着我。我惧怕黑暗,因为它淹没了我的所有希望。
她陆陆续续给我寄过几次钱,但从来没有写过一封信。我知道,她可能是怕触及伤心事。每次,我都到邮局办理“查无此人”的退汇手续。我爱她,但感情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没多久,她就杳无音讯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是地主出身,又被怀疑是苏联间谍,自然是专政对象。我被关进牛棚后,万念俱灰。如果没有对斯美塔娜的怀恋,没有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恐怕我早已不在人世了。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我的生命里只有她。
日子就如僵尸般一天天过去。有一日,井下瓦斯爆炸,我不顾自己的身分,极力反对封井,主张利用北风抽取、稀释井下瓦斯。几百名矿工得救了,我也因此将功赎罪,恢复了技术员的身分。
我的心静如一潭死水,每天重复着过日子,像个木头人。
不能让人忘怀的是让我起死回生的那一天。一日,老矿长偷偷地交给我一封信,她的信!我日盼夜想的斯美塔娜啊!这封泪迹斑斑的长信,记述了她的思念和爱恋。她说父亲因心脏病猝死在批斗台上,有人说他是内奸和叛徒。她说她对不住我,对不住父母,她的压力太大了,她没有其它出路。她要我理解,我仍是她今生的最爱!
读着信,我双泪长流,积郁多年的感情喷薄而发。魂牵梦绕的情与爱啊,终于又活过来了!
信的末尾,她说她不久要来中国,届时,约我去满洲里和她见面!我欣喜若狂,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老矿长很了解我,他与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商议再三,决定派我去离满洲里不远的一个矿务局出差。
斯美塔娜是以苏联外贸部检疫局官员的身分到满洲里验货的。我和她在一间林中小屋见了面。劫后重逢,千言万语却不知说什么好。
她这次专程来中国,就是想跟我怀上一个孩子,以了却她的心愿。
我心里很是矛盾,我还在爱着她,但中国人所固有的道德观,使我不得不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心理上的平衡,以致于她在我怀里抽泣不止、语无伦次地热吻着我时,我真的束手无策了。我只好借故说:为了我俩的情爱,我已被折腾得九死一生了。你看,我浑身是伤,人未老,心已衰。现在生活好不容易渐渐走上了正轨,对婚事已经淡泊,心静如水,望能看在旧情的份上,不要再来打破我这来之不易的宁静。
斯美塔娜听了我这一番话后,说出了她的肺腑之言:她说她要是只为了生个孩子,在苏联国内可以找到无数的良种“公牛”。她不顾一切从万里之外来找我,主要是因为我最有资格成为她真正的丈夫,成为她的可怜的孩子的父亲。我与她还应有一段孽债未还清,她还要做我的没有名分的妻子,否则她一生都会怨悔,愤愤不平。这是上苍的安排。
“思凝,你不是最相信命运和缘分吗?这就是命运和缘分,是我俩的命!我俩的缘!我们俩赖也赖不掉,躲也躲不脱的。”
她的话令我热血沸腾。我的泪一滴滴地滴在她那大而圆的眼睛里,汇成一串串珍珠挂在她那苍白的脸颊上。
我不知道是她的泪还是我的泪。
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再也不能自已。
事毕,我丧失了理智,发疯般地奔向密林深处,漫无目的地在林中不知游荡了多久,最后晕倒在一块草地上,直至大雨把我淋醒。我知道,这一次,我和她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
后来,为了彻底解放自己,我决心回湖南老家去隐居。我给矿领导打了一个冠冕堂皇的下放报告,主动回乡务农,在农业劳动中接受再教育,洗涤灵魂,重新做人。
下放报告很快就批了下来,我回到了湖南农村老家。这真是:
三分旧情留满洲。
七分无奈下潇湘。
回到湖南农村不久,父母先后亡故,我成了孤儿。先在乡镇中学代课,后成为民办教师,再转为正式国家教师。在清贫的生活和繁忙的教学中,我把所有的情和爱都用在了学生身上,就想这样独身一人活下去,直到走进坟墓。
当我年近45周岁时,也许是天意,一个女生爱上了我。我们结了婚,她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儿子已14岁了。
最近,斯美塔娜从老矿长那里打探到我的地址,寄来一封信,随信还有一张照片。她到底是老了,一身的珠光宝气掩不住岁月的沧桑,但她看起来更高贵、仁慈。她身旁站着一个黑发小伙子,上唇留着一撮浓密的胡子,像极了电影《静静的顿河》里的男主角葛里哥利。
斯美塔娜明确地告诉我,他是我的儿子,是满洲里的结晶。她还征求我的意见,能否接受她五万法郎的馈赠?她知道我教书很清贫,现在唯一能给我的就是钱了。
我回信告诉她,不要寄钱,也不要把真情告诉孩子。我们活在世上做人不容易,让我们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宁静吧。
苦和悲都是人生的一种永恒的美。
我常独自一人坐在房内,任凭思绪飞奔:生活犹如沏茶,不管有过怎样的甘甜或苦涩,终会归于平淡。在质朴与平凡之中追求着、品尝着、坚守着,也算是一种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