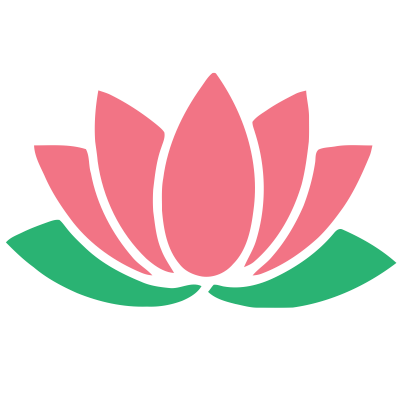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看完电影,父亲指着广告看板上“郑佩佩”三个字,告诉我:“你只要看到看板上有这三个字,回家告诉我,我就带你去看电影。”于是我开始认识字了。
郑佩佩是当时胡金铨导演一系列武侠片的当家女主角,一副侠女装扮,行侠仗义。我每天从幼稚园放学回家经过戏院,都寻找“郑佩佩”这三个字。
到了我会写作文的年龄,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贴出来或朗诵。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老师朗诵的作文,是“我的志愿”:我要做“侯氏企业”的企业家,坐着直升机去上班。
老师接着替我投稿到一家纸厂的内部通讯。稿子刊登了,老师当着同学的面交给我5元稿费。
后来,我说服了爸爸,资助我邮费,开始向外投稿。报社寄来的稿费,竟是10元邮票。我只好用来继续投稿。
不久,我开始办起地下刊物:《儿童天地》,从主编、采访、撰稿,到印刷、装订,全部一手包办。
《儿童天地》创刊号终于发行,一本售1元,印量25本;因为得不到级任老师允许,只能偷偷销售。拜我过去常常请客之赐,创刊号不但销售一空,还有同学响应征稿。统计盈亏,发现竟然赚了2元。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发行完第三期《儿童天地》,级任老师忽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去。等她看完了整本《儿童天地》,就转过来问我:“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做点更有用的事?”接着当然是一阵狂风暴雨:老师说出对我的期许,以及提醒我应走的方向。
我第一本体制外刊物,就在那样的压力,以及官方对我的期许之下,停刊了。
上国中之后,我在家里顶楼清理出一个小空间,一有空闲,就泡在那个天地里写稿,或者是疯疯癫癫地阅读我弄回来的书。
其中《背海的人》这本小说的第一页,满是脏话和三字经。这本书刚出版,我兴致勃勃买回家看,爸爸看见了,便皱着眉头问我:“你整天躲在这里,读这样的书,你觉得好吗?”
无可奈何,我搬回到只有教科书及参考书的书房,规规矩矩做功课,过正常生活。
过了一个月,我终于受不了,决定展开绝地大反攻,提出:如果我每次都考前三名,爸妈就不要干涉我的作息;考不到我就依照他们开出来的作息表生活,绝无怨言。
我花了一点心血,用最少时间,得到最好的成绩。下一次段考,我很意外地拿到了全校最高分。我的父母亲也吓了一跳。
我常想,要是我一直集中精力学习,事情应该会很顺利。不过我参与的事情越多,得到的警告也就越大。
我一直记得小学《儿童天地》事件,老师问我:“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做点更有用的事?”很奇怪,高中老师也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老师不断提醒我,空有才华是没有用的;他们总是细数一些从前搞社团、搞刊物的学长,如何荒废了学业,如何考不上大学,如何走投无路的故事。
如老师所言,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有一个学期,只得到第13名,是我考试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的惨剧。
有一位文史科老师对我说:“你是块特别料子,我觉得你应该鼓起勇气走文史哲的路。我相信你一定有机会闯出个名号来。”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我却没感到兴奋。
那时候我想:如果我的一生是个医师、工程师,临终时至少知道救活了哪些人,完成了哪些工程。可是如果我是作家,会不会只留下一些没有用的喃喃呓语,连自己都没有把握是帮了人,还是害了人?
我终于拒绝了这位老师的建议。
高中最后一年,我停掉所有课外活动。8月份,我的名字出现在大学联考医学系的放榜名单上,爸爸很高兴,在家门口挂起了一串鞭炮。
后来,我当上了医师,成为新进的麻醉住院医师。
我在产科值班,常常碰到一生下来就呼吸窘迫的新生儿,必须紧急插管;生死可能只系于几十秒钟之内。做这类插管,我总是双手发抖,患得患失。
有资深同事对我晓以大义:“你千万不能当他是婴儿,就当成一件事情好了,不要和人命扯上关系。”
“可是那是活生生的婴儿啊!”
“要你插管成功,他才活得成!如果你的任务没有完成,他就是个死婴。大家对你的期望很简单,完成任务,没有人期望你去担心或者同情什么。”
这种思考方式有助于我去专注做事。我试着忘记那是婴儿,也不再想起他的母亲、父亲或任何相关事情。我只是使用咽喉镜,直截了当地插管,完成任务。我的手不再不自主地发抖。不久,我就可以自在地完成任何困难插管,收放自如了。
我甚至决定亲自替老婆雅丽做剖腹产麻醉。我觉得医师如果无法从对亲人的情感中抽离开来,他的专业根本经不起考验。
我当住院医师时,重新有了写作冲动,一有空就在家里埋头写东西,有了一些受到欢迎的作品,像《亲爱的老婆》、《大医院小医师》、《顽皮故事集》等。
到我刚升上主治医师,急于建立权威,总是带着许多住院医师或实习医师到病房里去会诊。
病房里一个孩子是我的读者。我必须承认自己有点偏心,喜欢到这小孩的病房去查房,一方面因为他读我的书而感到高兴,也因为我开的止痛药每次都在这孩子身上得到最好的反应。
每次我带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师会诊,总会特意绕到他的病房,意气风发地做我的临床教学。虽然我注意到他越来越衰弱,可是他在疼痛控制上的表现,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那个孩子临终前想见我,我已经忘记那时候在忙着什么,没想到竟然错过了。
孩子父母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拿出一大包东西交给我。“他不准我们拆,也不准别人看,要我们直接交给你。”
我拆开包装,发现整包都是止痛药丸。孩子急于临终前见到我,原来是由于他一颗止痛药都没有吃;为了替我维护尊严,想在死前偷偷把止痛药还给我。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冲击。日复一日,我努力学习那些优雅的姿势与风范,竭尽所能治疗我能够治好的疾病;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无情自私、只看到自己却看不到别人的医疗从业员。
那时我搭上了顺风车,书籍一路畅销,一会儿被选入年度杰出成功人物、年度畅销作家,我的书也被评为最有影响力书籍,还有商业杂志分析我是如何成功地使用媒体及公关策略,完全超乎了我能控制的范围。
希腊神话中有个大盗名叫普洛克路斯忒斯。他折磨人的方法很著名:一张铁床。所有被迫躺到铁床上的路人如果身高比铁床长,他就将多余部分锯掉;身高如果比铁床短,他就将之拉长。
我有点像是躺在铁床上的路人。我要不是太高,就是太矮,每次都得扭曲自己一点点。一方面我并不觉得舒服,可是从另一角度看,大家都恭喜我成功了。而我在想,或许我还不够成功。我激励自己,不但做更多,还要更好。
回想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主治医师,进入研究所攻读博士,一路升职,工作应接不暇。
有一次,荒野保护协会的徐仁修老师告诉我一段在中南美洲旅行和原住民接触的经验。
“原住民向导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看着手腕上那个奇怪的东西,才决定要不要吃饭。我于是告诉他关于手表与时间的关系,让他了解,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们要吃饭。
“原住民朋友拍着手说:‘原来你们为了荣耀太阳而吃饭。’而他们吃饭的原因就是:肚子饿。”
那向导甚至坐下来等香蕉成熟,他会说:“我们等田里的农作物成熟,等肚子大的老婆把孩子生下来,等孩子长大,等着衰老、死亡,我们一辈子都在等待,为什么不能坐着等香蕉成熟?你们到底都在急些什么?”
我惊觉到我们匆匆忙忙,没有一刻可以浪费,都是为了荣耀时间而工作。
我第一次想离开医学,是大学四年级基础医学课程刚结束时,想去美国加州学电影。
十几年后,我渐渐成为资深麻醉专科医师,老婆第二次听到我要离开医学。她只是好奇地问:“你不喜欢麻醉这个工作?”
“我没有说不喜欢,只是想有更多时间写作。”
“你可以同时写作又当医生,不是一直做得很好吗?”
“我只想做些内心真正想做的事。”
“我总觉得好像还少了些什么,”雅丽笑了笑。“不如你先把博士学位拿到了,再决定该怎么办。”
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综艺节目里玩着“恐怖箱”游戏:来宾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伸手进箱子摸索,猜测里面的东西。
有趣的是,不管是什么东西,那些歌星、演员全都显现了程度不一的惊恐反应。
其实,我们恐惧的,是捉摸不定的未知。
雅丽问过我,如果有一天,我变成潦倒怨艾的过气作家,会不会甘心?
我想,如果勇敢地做了最坏打算,选择自己所爱,就算在人生的恐怖箱里摸来摸去,摸出了一个潦倒怨艾的作家结局,那又如何?人不断地老去,散去,生病,死去,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都挡不住,那又有什么好怕呢?
大概只有我们停止了恐惧,才能全心全意去享受人生这个大箱子里面所装的许多宝藏吧。
如果我因为恐惧而不敢选择自己所爱,那样的人生走到底,我该怎么跟自己交代才好呢?或许幸福比我们想像中的还要简单吧。
36岁生日那个晚上,我又向雅丽提出要离开医学。
雅丽举杯祝我生日快乐,然后说:“既然如此,你明天就去辞职吧。”
我吓了一跳,问她:“你同意了?”
“过去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听你一再提出要离开医学,我忽然知道那是些什么了,”她笑了笑。“看到你对自己的未来有向往与热情,我觉得放心。”
“可是你先前提出来的问题……”
“我提出那么多问题,只想给你一些提醒,确定你都考虑过了。现在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的天才梦,也许不过是天才妄想、梦幻破灭的故事。不过,即使在梦幻破灭的尽处,我也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对生命的质疑与好奇。
每一瞬的生命于是有了梦想,有了探索,有了一回又一回的想像与发现。
侯文咏
台湾嘉义县人,台大医学博士。目前专职写作?、兼任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万芳医院、台大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